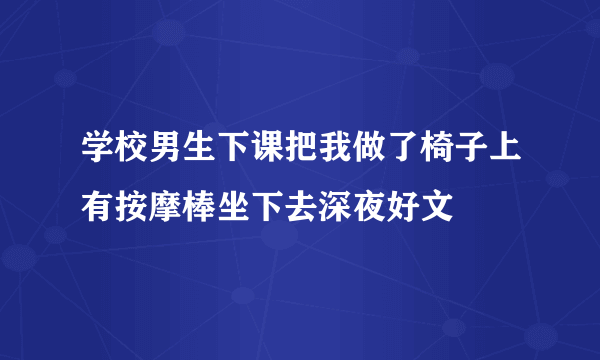七环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一"七环,我们搬家吧。"我摸了一把额前渗出的汗水,轻轻地对电脑前的七环说。夏日焦躁不安的气息随着吊扇的转动,在空气里一张一翕地浮动着。七环淡淡地望了我一眼,没有吭声。瞳孔里反射着电视机雪花点的空洞。我知道七环并不想搬家,他已对这病态的出租屋产生了病态的依赖。破旧的出租屋病态的裹挟着我们这样一对情侣,我渴望从这种种病态中逃离。出租屋不大,却是北京七环路*上的常有规模。国道汽车驶过的哗哗声,隔着单薄的墙板传入耳膜,清晰可闻。此后脑海里一时间都随着马达尘土飞扬。不过这喧闹情形并不多见,出租屋的常态是被淡蓝壁纸包拢在一片可怕的沉寂之中。最可怕的是屋子里慢慢长的消弥的余音。那是极其内敛却极其张狂的强烈长鸣。它像一把刺刀直指我的耳骨,刺磨着我的皮下神经,刺磨我每一个脑细胞,他们向一方拥挤,又被强行割裂开来。二第二天醒来,我躺在医院的隔离室里。和往常类似,在陌生的出租屋里经历一场无法回忆细节的梦。这里生活的病人大多没什么身体上的疾病,铁丝网笼罩下的病房有力地证明了这里是一家精神病院。曾经,我,国家射击队的一名队员,成绩向来优异,倒也从未在练习和比赛中有过失误。在一次比赛失利后,我患上抑郁,并在精神有失常迹象后来到这里。我永走不出那次比赛了。对于一位专业的选手,一次七环的成绩,成为我一生失败的烙印。精神失常前,梦中最后的时刻是急速下坠的过程。高空坠落的物品总是摔得七零八散,血肉横飞。人们习惯把曾不可及的东西踩在脚底。大概正因此,病房前护士们常用眼斜斜的看着我。她们刘海旁的细碎头发,把促狭的笑容遮挡得更加明显。紫红色的嘴唇,像两片切开的短肉肠一样拼在一起,从而挤出一个麻木而辛讽的弧度。护士们吞吐着鼻尖冒出来的空气,那种气体随着整个身体开始摇摆。我无法觉察到她们身体所展示的完整韵律感,但可以清楚捉摸到的,是她们的面部一一那些极其聪明的肌肉,又开始别样的抽动。"你的七环呢?""吆,今天怎么不喊七环了""现在又正常了?"她们笑着走开了。但无所谓,面对他们冰冷的讥讽,我报之一笑。但是这些日子的梦太长了,更奇特的是,那些梦实在是太真。自己和一个陌生男子生活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那里的墙纸相当可怖,房间四周贴满可以密闭我所有呼吸的蓝色。我望着病床床头护士们特地挂上的那块箭靶,它被医生摘下,却总是又出现。那些颜色不一的同心圆叫我被卷进熟悉而陌生的漩涡。我做大量的梦,然后努力控制出一些无法与语言规则相妥协的话语。我总兀自矛盾,然后兀自挣扎,兀自狂奔后却兀自跌落。我病情的审查报告显示的永远是错误的诊断。我知道我的精神状态只是偶尔在正常与不正常间有一些切换。有意的,无意的,一切梦的始端都伴随着急流的旋涡,无助中,我想起先前的一位教练,他对我是那样的好哇。有一次,那时候我很小,刚入队,却因体能不合格而蹲在那里哭,一直哭。在这里,没有人会相信泪水。他却觉得我天赋异禀,过来安慰我。 并且帮助我一步一步提升水准。最后我也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十环,每次都是十环。无论怎样出手,我都会令我自己满意。然而就只有那一次的错误,我永远记得那样一个时候。我恨不得用手把箭的路径生生掰直,可惜它就是歪落在那里。那时,一股暗黑色的,无比滚烫的激流,在虹膜前左右横扫,扫荡出出租屋的蓝色。叫我永远不得清醒,嗡嗡嗡,各种声音在我眼前响起,电扇声,汽车声,护士的笑声……所有,都变成了奇异的融合。我想见到我的教练,我真的太想见到他了。也许他可以帮我,也许我还能重返赛场,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被重叠的梦境所绑架,精神压力或许会减少一些。死马当活马医,我还是去求了那些护士们,起初自然没人愿意理睬我,她们的肌肉仍然是那样快速地抖动。不过后来一位稍微和善一些的护士勉强答应了我,帮我给教练拨打了电话。"喂,教练,我是…"我像一个悬崖旁的人,紧抓着最后一根绳索,唯恐坠落。"…"绳索咔嚓一声,断了。那样和善的教练不假思索地挂断电话。"咚一咚一咚一"咚…咚…咚…那些东西在我眼前突突的跳跃,模糊了我的视野,世间的一切此刻都失掉清晰的棱角。它们卷入环形的线中,所有波涛变得滚烫,泛起无边的蓝。我倒在医院的病床上,眼前一切都开始旋转,在蓝色的波涛中旋转,我闭上双眼,醒来,眼前仍是蓝色。就像出租屋的墙纸,无边的蓝,无孔的蓝,密不透风,包裹电扇的旋转。一切实在是讽刺,人类行为的目的性那样明确。没有天赋便会失去青睐,没有身份便会失去尊重。一切都在虚假兽性的包裹下蛰伏。失败后的嘲讽和嘲笑又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回荡。我渴望并努力地掰断着病房前的铁丝网,在值班护士睡觉时找到病房铁笼的钥匙。真正的兽性成为我血脉中来回流淌的河流。三难以想象这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她的谈吐那样亲切自然。我因鼻血流失过多而在家休养一天。没想到,编辑部人手不够,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接受了任务一一观察并记录一位因网络舆论而出现精神异常的女射击运动员的现状。越向医院深处的病房走去,消毒水味就越来越浓。此时,原本黏呼呼的鼻血从鼻腔里推了出来,我赶紧扯了一把纸使劲捂住,血腥味终于变淡了一些。那是一个极为空荡的病房,一个女人轻轻靠在医院的蓝墙上。隔着铁丝网,她的眼神渗透出疲软。头发从头皮中抽拨出奇特的香气,这和淡淡的血糊味融合在一起。那些香味从头发丝的缝隙中泻下,在冲出发梢的那一刻,立即冲破了空气中的平淡。我并不很能够捉摸清楚这位女运动员的神态,吸引我的倒她的嘴唇。黄色的组织皮层颤颤巍巍地蜷缩在嘴角,或是胆怯的附着在厚实的唇瓣上。风一吹,那些脆弱的皮层,上上下下地摆动。她平静地向我诉说着她的精神状态。这里的护士都欺负她,从未给予过她应得的尊重。教练也为了逃避麻烦,毫不犹豫的挂断了她的求助电话。这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精神是正常的。但我知道,她的确是病了。来到这里之前,她的教练每周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她,并时刻观察着她的病情。而那些护士们每天都细心护理,她们从我刚进门开始就报以友善的微笑。曾经那些网络上残酷的舆论给她带来的伤害有如洪流猛兽,这让她并不复杂的精神世界从完整的大陆破碎成无数孤岛。所有压力转移给这里每一个无辜且善良的人。尽管她的一切叙述看上去那么合理。下午一点,护士照例给她注射药物。不知为何,她的眼中闪过无名渴望。鼻xue从吞吞吐吐的抽哒中大肆喷涌。她张开嘴,疯狂大吼,温软的发丝那一瞬间直立起来。安静被突如其来的怪异所划破。她不知用什么方法拿到了钥匙。铁丝网打开的瞬间,xx的味道氤氲整个病房。她举起剪刀,那位护士的胸口顿时xxxx她向那位倒下的护士喷吐着口水。白色的线条从空中落下,红色的河流迅速蔓延开来。病房中充斥着人们的惊叫。那些鼻xue,在鼻骨中停止喷涌红色的激流。一时间,脑海随着红流的模糊在病房中围绕着环形的线运动着。没有铁丝网的笼罩,我终于看清了她的神态 ̄ ̄她冲我笑着。*七环路:北京市规划无七环 ,本文为情节且表达主人公挣扎精神状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