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忠镐院士:我是穷人的大夫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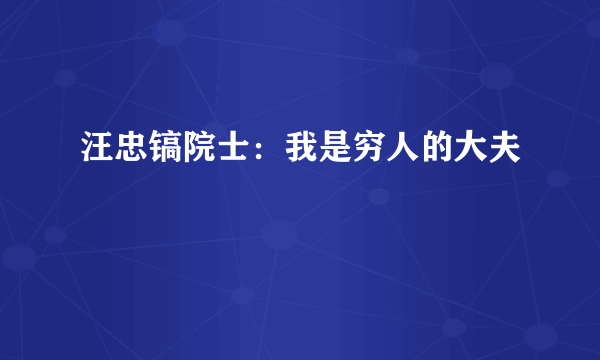
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就是要为别人做点事,我也知道我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也知道自己太累了,我也问过自己是不是该歇歇了,但一看见病人就歇不下来了。
好医生就要善于为病人动脑筋最近身体好吗?
记者问汪老。
汪老掏出化验单说,好什么,手术后饭吃得少了,血脂却比平时高了4倍。
汪老因疑似哮喘,在去年第5次住院后被下了病危通知单,然而他不仅在为自己作出诊断后奇迹般地好转,还在去美国治疗前的住院期间,坚持为患者做了几例大手术。
他说,如果没看见就算了,一旦看见了,无论什么情况,我能解决的都要替病人解决。
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就是要为别人做点事,我也知道我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也知道自己太累了,我也问过自己是不是该歇歇了,但一看见病人就歇不下来了。 事实上,汪老自行医以来,还从没有歇过的时候。
“文革”时,根据毛主席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汪忠镐参加了专门为贫下中农开设的“6·26病房”,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各科的工作,甚至连妇科和护士的工作也都做得得心应手。
当他为一个患者切下了重达4斤4两的肿瘤时,大家伙敲锣打鼓地为他庆祝。因为病人多医生少,往往最严重的病人都需要汪忠镐来治疗。
1971年,他为一位甲状腺肿瘤患者完成了一个难度非常高的手术后,病人的食道开始化脓,大家都觉得救不活了。
汪忠镐急得几天几夜合不上眼,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一个塑料管套上个橡皮膜,插到食道里再打入气体,终于把漏洞堵上了,这就是他的最早发明——自制球囊导管。这一技术经过推广,使救治率从36%提高至90%;用该法治疗腹主动脉骑跨栓时还避免了开腹,围手术死亡率从46%降至10%。
唐山大地震时,他又主动报名到灾区救治伤员,在学生的帮助下,一天就做了43例手术。
“文革”后期,已经结婚的汪忠镐在协和医院第一个报名到大西北“扎根”。
在治疗中,汪忠镐发现很多贫困地区的病人经常挺着充满腹水的大肚子前来就医,并伴有肝脾肿大、食道静脉曲张、下肢肿胀、皮肤溃烂等症状。
教科书上关于这类疾病的描述只有简短的一段话,一些大夫把这种病作为肝炎后出现的肝硬化来治疗,结果越治越糟,病人死亡率竟高达90%以上。这到底是什么病?
汪忠镐开始反复琢磨,在学生和同事的帮助下,他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做了68万人次的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在大量动物实验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这种叫布加综合征的病症是一种肝后段下腔静脉病变导致门静脉高压并伴有下肢静脉高压的临床症候群。
他对该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分型、诊治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创立了多种手术方式,在全国和国际得以推广,使该病就诊时所见的早期病例从10%上升到60%,病人死亡率从90%降到5%以下。
为此,1987年,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特邀汪忠镐做报告,并赠送其该校最贵重的礼物—一支“礼拜三领带”和客座教授称号。
牛津大学医学教科书专门引用了汪忠镐这一研究成果。美国脉管学教科书特邀他撰写布加综合征章节。 除了攻克布加综合征,汪忠镐还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大动脉炎脑缺血的架桥手术、瘤体切开-重建血管法治疗腹主动脉瘤等一系列开创性手术,并发明了许多医疗器材,先后成功申报了10多项国家级专利。
汪忠镐说,在“6·26病房”和大西北期间,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贫病交加,什么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时经常是什么医疗条件也没有,就用当地可以找到的生活生产用具给病人想办法,从不断地治好病人中,我自己也建立起信心。
医生的技术是怎么提高的,我觉得就是逼出来的。
汪老生病期间,虽然他一再解释,但根据症状很多医生还是把他诊断为哮喘急性发作。但老人家认为自己每天夜里两点钟时会出现憋气、咳嗽、咳痰的症状,只要一坐起来就好很多的现象绝不是哮喘。
经过琢磨,他大胆地断定自己得的是食道反流导致气管受阻,提出“胃食管反流病不是哮喘”的新概念,并在二炮总医院建立了胃食管反流病中心。
“我不仅把自己治好了,还要把和我得一样病的人治好,这次去美国就是去研究食道反流手术的麻醉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到现在我已经治好了22个类似患者。”
汪老轻松地说。
“在患病中,我深深感到对于一个医生,医德和医技最重要。”
汪老说,年轻的大夫应该认识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医生,就要先培养自己的医德,有了良好的医德,就会不断琢磨技术,医技自然也就提高了。
我一生碰到了那么多的疑难杂症,但从没有推过一个病人,不推脱就要给病人解决问题,为此,仅做实验的狗我就用了近600多条。所以当医生,就要敢于负责,勤于琢磨,想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你的病人的实际困难提出来的,好医生就要善于为病人动脑筋。
在我生病期间,我特别痛心,怎么就没有一个医生,能把我的病情详细记录下来,然后再去查资料,认真地为我这个病人琢磨琢磨呢?
我代表恩师的水平在行医,绝不能含糊 “我看病是看不快的,”汪老说,“现在很多大夫即使病人住院了,也很少去问问病情,而我看病是很麻烦的。
以前看门诊时,我需要3个学生帮忙。
他们仔细询问病人得病的前因后果和具体症状,然后,我们再逐一分析,所以我看病通常只需要病人来一次就可以给他定论。
我曾师从老协和的曾宪九、吴英恺和裘法祖等医学名家,他们看病,绝不仅仅看看片子就可以了,而是问清来龙去脉,了解现状,分析各种可能性。
对恩师们,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我是代表恩师们的水平在行医,绝不能含糊。”
曾宪九教授是汪忠镐在协和工作时期的指导老师。在胃癌研究过程中,他不仅手把手地教导汪忠镐,更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每次汪忠镐主刀动肠胃手术,他都充当第一助手。
修改学生的论文,大到医学问题,小到文法细节的错误,曾老都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改正。
“一次,曾老给我的英文论文里加了一个单词,individual(即个体化),”汪忠镐说,“老师为什么要这么给我改,我仔细琢磨,结果发现,经曾老给我加了这个字后,文章内容的表达更加准确,意义更深刻了,文笔更生动了,别小看加的这一个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一辈子受益。
在到协和之前我没学过英文,正是通过这种一个字一个字去学习的方法,到现在我已经发表了100多篇英文论文。”
1984年,七旬高龄的吴英恺教授要创办安贞医院,为了建好血管外科,吴老亲自四顾茅庐请汪忠镐加盟。
汪忠镐说,其实老人家第一次来我家,我就同意了,但因为安贞医院离我家太远,我爱人不同意。
吴老第四次到汪忠镐家,是个星期天,老人家走时,汪忠镐和爱人把他送到公共汽车站,人太挤,最后两人只能把老人家给推上车。
汪忠镐感动了,他于1986年正式转入安贞医院。
提起裘法祖教授,汪忠镐说,老人家如今90多岁了,依然在查房,跟他比我差得远了。
在我面临很多医疗学术的争议时,裘老都挺身而出,用他的知识支持我。我这次生病,裘老为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在别人均不同意我的结论时,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
我这一生都在用他的一句话来要求自己:做人要知足,做事知不足,做学问不知足。对得起老师的是,我觉得大致上我还是做到了。
裘老还曾说过,不近佛者不为医,所以每次有患者给我红包时,我都坚拒,现在很多人说,要查医生的收入,我敢说,要查就先查我好了。
如今,汪老已年近七十,但他说,我还觉得自己刚离开校园没多久,恩师们的教诲犹如昨日般响彻在耳。
他至今都记得在协和病案室里看到的上世纪40年代曾先生、吴先生等老一辈医家书写的英文病例,从文法到图表都是精益求精,让人叹为观止。
“协和医院有三宝:病案室、教授和图书馆。协和给学生提供了宝贝,但去挖掘还要靠自己。
从恩师的一言一行中,我学到了他们慈善为怀的医德、娴熟的技艺、正派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辈子除了医术,我从不想和别人争什么,我到哪里从没有经济架子,但我有一点学术架子。”
为了国家,我绝对可以去拼命 在采访中,汪老流了两次泪,两次都是因为他提起了我们的国家。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汪忠镐出生了,日本人打到了他的家乡,不甘做亡国奴的父亲带着全家老小开始了三次逃亡。
一次,一家人藏在坑道里躲过了日本人的追杀,当时汪忠镐只有3岁,妹妹只有1岁,如果有一个哭了,一家人全活不了。
从坑道里爬出来赶路,一路上遍是同胞们的尸体,逃到浙江南部时,汪忠镐问爸爸,为什么整个县城都是黑色的,父亲无语了,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日本人“三光”政策带来的恶果。
“所以我对敌人充满了无限的恨,为了国家我绝对可以去拼命。而对受苦受难的同胞我充满了无限的爱,没这种经历的人是不会理解的,我们的同胞需要去同情去拯救,而不是从他们那里去攫取,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会做。”
说到这儿,汪老攥紧了拳头,热泪充盈了眼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汪忠镐曾亲自主持过10多次国际会议。汪老说,在国际会议上,在与别国专家辩论时,我绝对以我们的国家为荣。
汪老当选为亚洲血管外科协会主席时,上届主席以当选为筹码向他指手画脚,并表示如果不听调遣,当选就要出问题。当时,汪老微微一笑说了句,Idon’tcare(我不在乎)。而第二天他正好要在大会上发言,发言最后,老人家即兴宣布:明年在中国我们将召开国际血管外科大会,此话一出,上届主席目瞪口呆。
为了证明中国是否有能力召开国际性大会,他亲自来到中国考察,看到了汪老拥有那么多不同病症的病人,他无言地离开了。
汪老说,我就奇怪,中国人去国外干什么,我总觉得只要我还在,就要在中国,需要我的人在哪里,不是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
虽然有十几家国外高校聘请汪老去做客座教授,但他说,我把这些都只当成是对我的认可,我到国外去就是交流,把好的东西带回来,同时也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也有好东西。
10年前,汪老参加在香港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中国去了100多人,但没有一个人发言和提问。会议的最后一天,汪忠镐走上了讲坛,潇洒流畅地做了一个大报告,结束后,在场的中国人一拥而上,把他抱起来抛到了半空。
汪老说,虽然有很多学校请我做客座教授,但我最骄傲的是1979年我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访问学者,但6年以后再去,我就成了客座教授,我觉得我特风光,我给中国人长了脸。
汪老至今已经去了16次日本,但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富士山是什么样子,除了与同行交流,他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