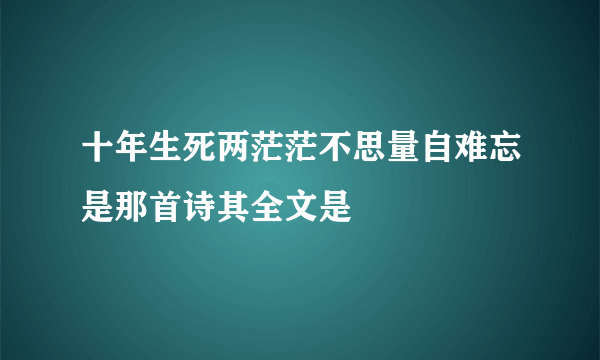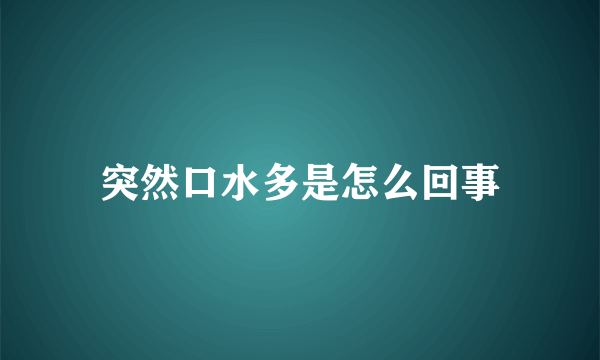突然十年便过去读后感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突然十年便过去读后感
小说的主题、主线、甚至主角我都还不清楚,只是知道开始的一幕必定是一场葬礼,一个父亲的葬礼,儿子刚好撒下一铲土,而视点居然是从下而上的,看到零零碎碎的土扑面而来,破裂了一片蓝天。
因此,我知道那是我对父亲的愤怒。他在我两岁的时候抛下了我们,跑到我至今觉得遥不可及的地方,他和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隔一段时间寄回来家用,不够,不定,零碎的就像葬礼上的土。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已经不再愤怒。
在我刚满三十而又决定向他一样离开香港的一年,我以为我可以像另一个成年男人般的与他对话。但他,已经变成了老年人。他回信了,罕有的,说不想再想起以往的种种,只想安静的度过晚年,因此,不想见我。
我在不甘与不忍之间,始终没有轻举妄动。
直到今年二月,我打了电话给他,竟然是因为我妈的死亡。我把消息告诉他,他大概也很错愕吧,然后问我,刚寄回来给我们过年的家用收到了吗?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一时之间,他如何承受而又做出恰当的反应呢,大概也不可能有任何恰当的反应。但我当时清清楚楚的感觉到我的愤怒,带着年年月月的重量,去到我的身体之巅。我的指头抓紧,我的舌尖快要裂开。
我姐姐看到了,把电话接过来,然后叫爸爸不要担心,我们会打点丧事,待一切办妥再告诉他。姐姐诡异的安静,对我说,这大概就是男与女的分别吧,女的,总是心肠软。
我不肯定我妈是不是心肠软。我只知道她必须以一种硬的姿态才能够过日子。毕竟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可以选择的姿态其实真的不多。妈很少谈到她的选择,有一次,在她没有八十也有七十的`时候,她说,当时没有改嫁,真笨。妈从来没有说过追求她的是怎样的男人,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几个。只是不断的告诉我和我姐姐不想我们变了"油瓶仔"。有时候也想,假如我真的有个继父我会不会因此少了一些对我生父的愤怒呢?唯一我比较肯定的,就是我必须记住我妈大半生没有白过,因此,我才不太责怪我爸。
于是,我决定书写,证实她的大半生没有白过。
在我妈去世之后,我没有想过些什么。终于执笔,有两个原因,一远一近。远是因为有人送了本书给我,我是PAUL AISTER的《孤独及所创造的》。我每天睡前都在看,但不出一两页就睡着了。又一次,我坐火车带了书慢慢的看,慢慢的,悲从中来。
作者写的是他刚去世的父亲。于是,我怀疑,我先前看一两页就睡着,不是因为我累,也不是因为书闷,是我逃避。而近因,就是《突然十年便过去》出版,编辑叫我写序。
我想,我妈,可能就是我的序。
要写好这个序,可是非常的困难。看,我从文首到这里,拐弯抹角,仿佛有一种逻辑,却也不无混乱,也许,就当是我妈对我的影响吧,假如她是前言,也不必然定后语。
纵然,在艰难的生活下,我相信她宁愿看有把握的故事,所以她喜欢荷李活片,尤其爱动作片和恐怖片,后来,我猜测她在电影里头那个说英语而简单的世界里,看到她的男人。我从来没有问她。而我从两三岁起一直带着我和姐姐去看电影,有时一天两场。我还记得奇连伊士活电影里的血迹,也我记得最后的一场和她一起看的电影是《2012》,当时她八十三岁了,外出都要靠轮椅,但那一次,她撑着拐杖可以跑到洗手间。我从来没有问她电影对她的意义,但我很明白是她生存的力量之一。
我从我妈身上渐渐体会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后来,我参与了流行文化,然后,也开始进行当中的研究。
当然,假如我的事业由我妈选择,她一定有另外的向往。
我写词写了十多二十年,她从来没有亲自让我知道她看过我的作品,只是偶然的会对我说那位亲戚那位邻居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学会了那是她表达以儿为荣的方式,至于念博士,对她来说,更是匪夷所思。我妈较多说的,就是仔啊仔,如果当天你留在政府工作,今天一定赚了很多钱了。
尽管如此,我妈从来没有阻拦我认为我重要的选择。
在种种小事情上,例如去哪家酒楼吃饭,什么时候应该回家,我妈处处显示她的霸道,也是焦虑。但在大决定上,她都由得我。我小学毕业,她想我报读工业中学,因为我们穷,可能我还未念完中学已经要出来工作补家计,有门手艺总是好的。但我没有听她的,后来,我选了文科,入大学也选了文学院,而不是她期望的法律系。后来,我才醒觉她一定非常的失望,当时我只管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
我叫我妈失望的应该很多,而我所知道的应该比她亲口告诉我的多。有一次家里不寻常的剩下我和她,然后她又说起我没有结婚生子的事情,说没有机会抱我给她的孙是她做人最大的遗憾。
面对如此粗暴的指责,我也只能还以粗暴。
我说,你当初不也是个走上异路的人吗?
和我很多我认识的家庭一样,我妈很少问她的子女提及自己的往事。例如她与我爸的纠结,从来没有告诉我。我只能间接听回来,加上自己的推理与幻想,然后就成为我所相信的历史:她还是少女的时候离开了自己的家,搬到了一个相熟男生的家,后来又跟他们一家去了香港,我妈本姓周,到香港后跟了这个男生一家姓成,谁知后来又改嫁了给姓周的,谁知后来这个姓周的与另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地方经营了另一个家。剩下她,与我,和我姐,在香港。
当中的曲折她都没有多说。我唯有认定她当时一定是离奇的少女。
而这个离奇的少女在认识她最后几年,变得充满牢骚,不是抱怨周身骨疼就是苦哀叹百无聊赖。她躺在床上的那种孤独,往往令我想起更早年的她,换了抑郁症,不是睡觉,就是骂人。
那时候我只有十多岁,突然失去了坚强的妈妈,因此我害怕软弱。有一次,我妈批评某个妇人,说她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我觉得她在说我,而后来,我又三番四次的神经质的证明我也可以此志不渝。
对于我妈近年的孤独,我无能为力。幸好她在体力还可以的时候,我说服她来阿姆斯特丹探我。那一年的夏天特别明媚,她开心的坐在轮椅上跟我们到处观光。我问她吃西餐还是中菜,她说,当然是西餐,中餐随时在香港也吃得到。有一个下午,我们坐在路边的咖啡店,我妈对旁边一家杂货店很有兴趣,于是一个人撑着拐杖蹒蹒跚跚的走过去,尽管语言不通,她还是满载而归。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如此活泼,如此有生命力的妈妈。
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送别的时候,我强烈的觉得,可能我不会再见如此的她了,我不知所措。我妈握着我的手,说:仔,我知你乖。
我常常觉得"乖"这个字很奇怪,就像是缺了什么似的。对,是一双腿。可能是我先学会了"加减乘除"的"乘"。而假如我是乖仔,我妈是不是良母呢?然后,我发觉,跟"乖"一样,"良"对我来说也是不完整的字,我想到了"娘"。我不是不明白,女良成娘,但我更觉得是娘必须抛弃作为女人一些珍贵的东西才成就了良。
所谓的美德难道都是残缺,都需要抛弃才能成就的。
那一天,我为了思念,跑到一个我认为最值得我坐下来思念的地方,从傍晚一直到天黑,暮色居然爬到了我的眼里。我在纸上试图写下我所有关于我妈的事。
这页纸后来放进我新买的牛仔裤袋里。
染了蓝。
纸上很多的笔记,银镯子、耳挖、萝卜糕、新师奶…我都没有写下来。先前撒下一把土,后来一点一滴的执拾起来,这样的事谈不上完成不完成。
只能继续。
纸上若隐若现的蓝,就像当时一个约定。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里有句话说的很好,试图说关于任何人任何事都是一种虚荣。
于我,虚荣也许是我稍有把握的真实。